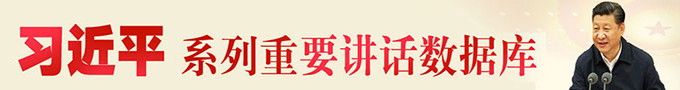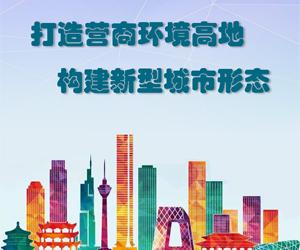酒,小卖部买的,杂牌。灌在军用水壶,方便,安全。香烟,大鸡牌,山东产,两块五一包。
胡继勤,老胡,我战友,同龄,同年兵,而且是老乡,都是安徽人,一同分在营部巡逻队,白天睡觉,晚上值勤,查岗查哨,防火防盗。写这篇文章时,他已经转业至海南某厅。
借着月光,我看到老胡眼里的疑惑。“小芳,什么情况,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过小芳?”
“一个笔友,聊城的,叫朱桂芳。你可记得,前年(1993年),我们俩晚上值勤巡逻的时候,不是经常听收音机吗?有天,我听到她在电台里面征友,后来依地址给她写信了。去年去靶场的时候,她还为我点了首歌,可是我没听到,有战友告诉我,让我激动的不行。”
“好小子,艳福不浅啊!”老胡坏笑
“回来后,我去信问她,果然是。我还责怪她,怎么不提前跟我沟通下,我也好听听你给我点的什么歌呀。后来准备考学,不是有时政内容吗,”我看了一眼老胡,“你不记得哪?你当时看的那些《半月谈》就是她给我找齐送来的!”
“怪不得,当时我问你是怎么搞到24期的《半月谈》的,你还保密,说是济南旅部战友给你准备的。哈哈,还战友?我看是被窝里战友吧?”
“别瞎说,纯洁着呢!别玷污我们感情好不好。”我阻止了他的插科打诨,“她听说我要考学,需要全年的《半月谈》,就告诉我说她爸在机关,应该有。所以她就想办法给我找齐了。春节时,我不是在教导队参加预提班长集训吗?她带着书来找我,没想到那天下午我正好去五营战友那里玩,同班的战友找我半天没找到,她在我们班坐了一会,没见到我,留下书就走了!”
“啊,没见过面?”
“是的,没见面,一直都书信联系。”我说,“就这么个情况。现在,你我都考完了,就等着成绩了,所以我想去找小芳,一来把书还给她,二是见个面好好感谢人家!”
“那必须的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去?”
“明天就走!”
“好,你放心去。白天我们都休息,应该没什么事。万一领导有什么情况,我替你打掩护!”
1995年7月28日,我带上1994年24本《半月谈》踏上了找小芳的路。你可能会问,咋记得这么清楚?不瞒你说,我有个习惯,写日记。都是有文字记载的。
起床号没响,我就从半山坡的炮阵地溜出营房,因为那里没有围墙。那时,我们部队驻扎在山东省长清县东南方向一个山坳里。当时我给他总结,三面环山,一面不朝水。根本就没水。整个营房,住着我们三营和四营。我的职责就是夜晚巡逻,应该没有人比我对地形更熟的了。因为没有请假,不敢走大门。这属于私自离队,如果被领导发现,那可就是一个大事情,更何况刚刚结束军校招生考试,千万不能发生其他什么变故。但一想到远方的小芳,身上背着的谈谈,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兄弟,走吧!
往西,是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,也是出营房的唯一通道,千米左右就到了公路边。从济南过来的车很多,去济南的车也不少。终于等到去聊城的中巴车。上车。走归德,过孝里,经平阴,跨黄河,路东阿,到聊城。此时,已经中午12点左右。下中巴,叫上出租车,到东昌西路XX号XX茶行。师傅很好,转眼就到。如果地形熟悉,早知步行,何必花这4元钱。4元,多,不多也。毕竟我每月津贴也就35元。
进门,两个女孩正在那忙着做午饭,我从背后一眼就认出了小芳。为啥?有照片呀!但我没敢叫她。另外一个女孩过来问我,“买点啥?”“找人!”“找谁?”“我叫范家生,找朱桂芳!”“咣当”一声,我就看到小芳把手边的油壶给碰掉地上了,旁边的女孩一边立马跑过去把壶抢起来,一边大声地说:“俺的娘呐,看把你激动的!”此时,我看到小芳的后背和手都在直抖,估计是被油壶吓得不轻。半天,她才转过身,满脸彤红地看着我,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。
“没事吧,怎么吓成这样?”我问。
“吓得?!吓能把她吓成这样!激动嘀,天天叨念着你会来,你会来......看看,真来了,油瓶都不会拿了!”旁边的女孩心直口快,话语里都藏着笑声。
三个人一道吃完午饭,掏出包里的书还给她,我就准备回来。旁边的女孩说:“想天念地的,来一趟,也不再玩会!”小芳说,我带你转转吧。于是,我俩出门,推上放在门外边的自行车。“我来带你吧!”我说。“你来怎么能让你带我呢,还是我带着你吧!”于是,她就骑车带着我。女式自行车,架子小,可能我又重了点,她把个自行车骑得一扭一扭的,我不放心,就顺手把她腰给搂着。估计她骑得有些吃力,一路上,我都感觉她身子在颤抖,颤抖。我也就学着旁边的女孩口气:“俺的娘呐,你别我给带到湖里去。”就听她咯咯地笑,很开心地、发自内心的那种笑。但我说得可是真心话,因为旁边就是东昌湖,紧张的我衣服后背也全都湿了。幸好,不远。
我们停在东关大街西口。这里可能也是聊城最繁华的地方吧,人来人往,络绎不绝。我们俩肩并肩往东逛了一会,她就跟我说,回吧。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,她不会是怕被熟人给看到吧!于是,折回。“照张像吧?”于是,21岁的我,在聊城,光岳楼前,留下了一张推着自行车的照片。照像的师傅很会做生意,“再来张合影呗?多难得!”我看着小芳,她看了我一眼,低下头,双手搓着碎花短袖的衣摆,低声道:“下次吧!”后来,没有了后来;下次,也没有了下次。
回来的时候,已经快吃晚饭了。问老胡,没事吧?!“没事,能有什么事?!”于是,跟老胡吹吹今天的经历,老胡听后,啧啧,哈哈大笑,坏坏的那种。
8月30日,我离开部队到郑州高炮学院报到。和小芳一直保持书信联系,直到1997年4月。我给她写信,今年暑假我就去聊城,见见你的父母,确定一下咱俩的关系。她回信说要跟父母商量下。结果没得商量。回信,说她父母不同意她找一个军人。是她不同意,还是她父母不同意,不得而知。我当时就急了,准备给她打电话,但我们请假出去很困难。正巧,教导员让我到北院他家中整理卫生,因为当时我是中队文书,教导员把他家的钥匙都放在我这。于是,抓起电话就打。结果,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教导员就找到正在整理内务的我,“家生,你小子昨天给谁打电话了?害得我花了187元电话费。”“啊......我是打电话了,给部队个战友。”“打电话不要紧,但你打完电话给挂好啊。早上一拿电话才发现,还通着呢!”23年过去了,为这事,我一直感到愧对教导员。他叫彭迪,江苏人,对我特好。我第一件不是军装的衬衣就是他送的,我第一次吃橙子就是他教会的......每每,我都亲切地称他彭导。老大哥一样。现转业在郑州市某局。
人散了,情还在。于是,每次看到《半月谈》,我都会想起这位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女孩--小芳。2002年政治部搬家,我在柜子的底下发现一套1989年全年的《半月谈》,觉得非常有价值、有意义,于是一直带在身边。经历过那一年的人们,准确地说,是大学生,对那年发生的事情应该记忆犹新。而且,我利用在政治部机关的便利,每期都认真地看,用心地学,尤其是作为教育干事,有些内容还被我编入到部队的时政教育里去。2004年在连队当指导员的时候,更是把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。2006年转业到合肥市人社局从事党组秘书,专职写材料,更是把《半月谈》作为学习的必备书。再后来,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,无法享受到免费阅读的便利,于是,从2017年起,便自费订阅了《半月谈》《半月谈(内部版)》,还有《品读》,因为她也是《半月谈》出版社出版的。因为这本杂志,让我学到知识,让我想起曾经的小芳,更让我懂得感激,感谢,感恩,那些遇到的人,那些经历的事。
看到这,您应该明白了,谈谈与小芳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否则,乍一看这标题,估计你的喉咙可能会咕咚一声,会不会?想多了吧!是不是?谈谈,是我对《半月谈》的昵称。小芳,倒是确有其人。
谈谈,发行了四十载。因为小芳,结识了二十七年。小芳离开了,谈谈却越来越近了,越来越亲了。半月见次面,甚至通过微信天天谈。到底是谈谈让我认识了小芳,还是小芳让我亲近了谈谈?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:谈谈与小芳的故事。
 | 文化旅游
| 文化旅游